treasures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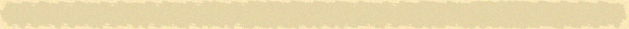
在當代學術界,對於北宋後期禦制瓷器的身世,即北宋官窑存在的真實性至今未有定論。反對者以未見窑址或少實物和傳世品難以界定爲由,否定北宋官窑的存在。類似觀點,曾經強加于唐代秘色瓷、北宋汝瓷等如今已釋疑的名貴瓷種。從考据學的角度講,以窑口的搜尋作爲判斷瓷種存在與否的依據,看似嚴謹,實爲形而上學,不利於啓發人們的心智,有礙學術發展。衆所周知,因靖康之難和其後的黃河改道,致使河洛一帶許多地面遺迹無存,探尋艱難事出有因。這就需要我們後輩研究者站在客觀的立場去小心的求證。
陳萬里先生依據北宋徐兢“奉使高麗圖經”,推斷汝窑貢燒于哲宗元佑元年至徽宗崇寧五年,已有共識。其時,距北宋亡覆尚有近20年的時間,以徽宗的清玩雅好和宮廷的需求而論,不會有空白期。在此,我想先就汝窑終燒作一番大膽的分析。汝窑的裹足支燒既克服了定窯芒口的缺陷,又保留了定窑裹足的特長,且“內有瑪瑙爲釉”,可謂精益求精,從而取代定窑,成爲禦用專貢。“汝州爲魁”,名動全國,各地名窑爭相仿效,趨之若鶩,進而對高麗等周力地區制瓷業産生重大影響。但是,從力學角度看,裹足支燒受力點少,胎骨易變形。從傳世品來看,汝瓷大圈足器居多,多採用足內側支燒,使器物受力均勻,儘量克服支燒應力集中的弊端,但仍難以避免斷紋和棕眼。此外,參考汝窑窑址發掘資料及實物標本,汝窑窑具和器物存在墊、支、又支又墊等多種形式,並非裹足支燒一種。可見,傳世禦用汝瓷的滿釉支燒確是曲意逢迎的産物,並非汝窑的全貌。隨著徽宗的即位,北宋皇室也愈發奢靡,受裹足支燒所累,汝窑貢瓷適燒範圍窄、成品率較低等弊端日漸顯現,已不能適應皇室日增一日的需求;其相對單調的器形和“素面朝天”的外表,更不能滿足那位文人皇帝的藝術品味。加之窑址不在汴京,貢燒多有不便,廢汝窑而于京師另立官窑也就順理成章了。南宋顧文薦《負暄雜錄》記載:“宣政間,京師自置窑燒造,名曰官窑。”該書冠以“負暄”的名稱,可見是作者晚年的隨筆。作爲當時的見證,人書俱老,應予征信。按照南宋葉真《坦齋筆衡》記載:“中興渡江,有邵局,襲故京遺制,置窑于修內司,造青器,名內窑。澄泥爲範,極其精致,釉色瑩澈,爲世所珍……”據此,宋代官窑的傳承脈絡清晰可見,從未間斷,誠乃繼繼繩繩,日益精進。“襲故京遺制”一語,再度證明北宋官窑的真實和重要。北宋末年汴京官窑雖只是流星一瞬,但卻閃爍出耀眼的藝術光輝,有著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。
北宋官窑的存在有著承前啓後的特殊意義。如前所述,汝窯以滿釉支燒聞名,而中興渡江後,“襲舊京遺制”的修內司和郊壇官窯則不見裹足支燒,卻代之以墊或支墊結合的方法,既是繼承北宋汴京官窯的余續,可謂淵源有自。
有鑒於此,在窯址不易或見的客觀現實面前,又應如何界定傳世的北宋官瓷呢?本人願意在此提供給大家一定的思考空間。
首先應該明確,北宋官窑存在的時間較汝窑尤短,更逢亡國滅種的北方兵禍,可以想象,北宋官瓷傳世應較禦用汝瓷更鮮。典章人物,掃地都休,何況區區一座官窑!宣政風流已不存,北宋官瓷又將焉附?需要指出的是,北宋官瓷源自汝瓷,其胎骨的選用和釉料的配置應與汝瓷相同或相類,主要區別,在於其裝飾手法的多樣化和支燒方法的改進。如前所述禦用汝窑主要採用單一的裹足支燒法,有其局限性;且以待詔供奉的身份,遵從皇命,不敢有絲毫失矩,更阻礙了汝瓷藝術上的發揮,其傳世品較少裝飾圖案,即是明證。這點不符合徽宗趙佶的藝術個性。
北宋官窑應運而生後,按器形的要求,對汝窑的支燒法加以改進,增添了墊、支墊結合的燒法,器物受力更均勻,使胎骨更堅薄,從而爲釉質更趨淳厚、勻潤創造了條件,真正達到了厚若堆脂的質感,器形也隨之豐富。與此同時,爲了遵從徽宗的藝術傾向,並凸顯北官的中心地位,北宋官窑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吸納了地方名瓷的裝飾技法,將帶有宮廷或皇權色彩的圖案靈活運用其上,極大地豐富了禦瓷的品類,這也是汝窑所不具備的特權。北宋官窑在燒制上的些許借鑒和大膽嘗試,一掃官瓷千篇一律的模式,明顯有別於南宋官窑,這可能與徽宗的文人氣質不無關係。因此,我認爲,可以這樣界定傳世的北宋汴京官瓷:胎釉應明顯區別於南宋官瓷而與禦用汝瓷相近;主要採用與南宋官瓷相似的墊或支墊的非裹足支燒方法,小足器物開始增多,即外支裏墊的形式;間或帶有裝飾。
任何事物都不是絕對的,在此我堅信禦用汝瓷、南宋官瓷存在特例。正如傳世禦用汝瓷多爲圓唇,臺北故宮則有汝瓷花口碗孤品;其他有無紋水仙盆、三犧尊等特例可資借
《中国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》备案号:京ICP备10029696号-1
聯系地址:北京CBD E-mail:wangpg1941@126.com
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0595
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0595